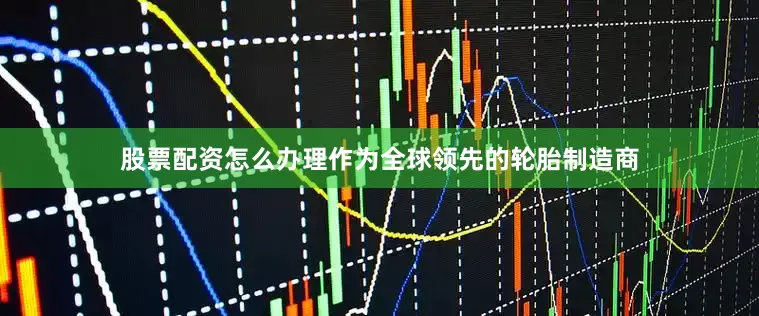我曾陆续接到电话,分别来自知名作家王林先生的子嗣王端阳与女婿杨福增。二人告知,他们正忙于整理王林先生的遗留下来的日记。这一消息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王林在1947年时任冀中区文建会主任,同年冀中区委设立了土改工作团。王林亲自参与了安平县的土改领导工作,并担任黄城片区土改工作队长。在这段时期,他与弓仲韬保持着较为紧密的交往。弓仲韬是黄城区台城村人,1923年3月,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同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首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别支部。我正致力于研究这段历史,因此,与此相关的史料对我来说异常珍贵。我请求他们查阅王林日记中相关文字,杨福增迅速将相关日记内容通过邮箱转发给了我。2023年7月1日,王端阳将经“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编纂的“当代民间史料丛刊”中收录的1946-1948年《王林日记》寄送至我处,这对我而言实为无价之宝。日记中关于弓仲韬的记载真实而宝贵,
王林1947年6月9日日记
......
昨晚,晚餐过后,文协小组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们将积郁多日的种种意见、成见、流言和传闻一股脑儿倾诉而出,实乃一大快事。然而,其中一条流言却让我一时难以平静,它指责我那件毛大氅是土改时期获得的胜利果实,并诬称我虚伪,明明是百姓之物,却故意说是学生时代的个人所得。方纪同志进而联系到我性格中的某些问题,猜测这或许是一种假装的严厉,用以吓人或炫耀。关于这条传言,我明确指出是孙犁或李黑所散布的,方纪同志则否认了孙犁的可能性,但对李黑则未作否定。显而易见,这显然是李黑的政治挑衅。其源头必然与辽城的某些旧事脱不了干系。那件大衣是我参与黄城土改后,从刘桂欣家中取出的,当时在车上,张根生便怀疑它是黄城的产物,因此后来他与县长一同在黄城也为各自置备了一件。我的这件大衣在北平时期,黄敬、周小舟等人都曾见过,这足以证明其来历。在黄城,我未曾动过任何一分一毫的私利……

◆王林
王林日记1947.9.26
……
又记:
弓仲韬抵达县城,对贫民小组代表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示强烈不满,情绪激愤。他指出,众多村民因私欲未能得逞,便对坚守制度的村干部心生怨恨。例如,许多所谓的荣军并非真正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
弓仲韬的正义之心强烈,然而他的学识却离不开村治安员弓春生的指导。弓春生虽然坚持自己在“五一”期间有所贡献,却因与群众脱节而颇受争议。工作团(县区干部)曾建议群众让他加入贫民组,然而贫民们却并不接受。后来,县里将他调至区委接受培训,弓仲韬(即弓春生)心中不禁怀疑这是否意味着他被排挤出了原来的岗位。
……
慰问团抵达,抗属们满怀期待,却因村干未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心生不满,今日遂以报复相向。村长杨栓公务繁忙,工作态度圆滑,因此得罪的人不多,在贫民组中的口碑反而不错。相较之下,春生因工作时间较长,群众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至于动员兵老干部,更是因为得罪了众多人,最终愤愤不平地离去。
王林1947年9月30日日记
弓仲韬于十二年正月加入党组织……所属党派为弓凤洲,所属团组织为卓之。因个人与村长产生矛盾,矛盾升级至反对贪污、查账。十四年,他组织青年会,要求增加粮食供应,由每亩三合增至一升。地主和富农试图雇佣外村流浪汉看守土地,但遭到本村贫民的抵制,未能得逞。十五年,在三联县委韩仲联家中,他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工会。十四年,他领导二十亩以下土地的农民进行抗差斗争,但最终未能成功。在民三、六、十二年连续遭遇大水灾害时,华洋义赈信用合作社进入村庄进行投资,以二十亩土地为抵押,可借得三百元,年息四厘,他号召群众进行抵制。十五年的夏季,弓璜(弓仲韬的长女,曾在北平温泉中学加入共青团)返回村庄,成立了共青团妇女部,发展了姊妹团,并创立了儿童团。工会组织的雇工增资斗争取得了胜利,工资从每年30-40元增至40-50元,之后又增至50-70元。十七年,他们还争取到每年增加一条白布和两双鞋。十六年,在弓仲韬的前院成立了平民学校,实际上是一所革命子弟学校。教师均为县委成员,以此作为掩护。十四年,又在弓家老祠堂开办了工厂,联络革命军人,试图组织红军,响应北伐军。国民党势力到达县城后,将农民协会改名为农林会,跨党分子纷纷分化。小范叛变后,曾直接前来抓捕他们,但机关并未设在此处。二十四年,吴立人前来找弓仲韬成立抗日救国会,还有两位地主一同参与。吴留下了二十元资金,其中一位地主也用了一些。这引起了另一位地主的反感。后来,有人得知吴是共产党,便对弓仲韬产生了埋怨。

◆弓仲韬
以下是对原文的改写:一是探讨冀中抗战史的撰写方法,如何科学地编辑史料;二是聆听作家们讲述他们的抗战经历。实际上,谈话内容非常广泛,没有固定的主题。我与王林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交谈,他谈吐风趣,记忆力强,语言生动。日记中提及的一些事情,他当时确实提到了,但描述得较为简略。因为这些内容与我的任务并无直接关联,所以我没有深入追问。
“你这是拿黄城土改的胜利果实来炫耀吧,真是太好看了,我们也得各弄一件。”张根生遂告知黄城干部,依照王林所穿大氅的模样,为他与县长各制一件,制成后自行付费。此事起初鲜为人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添油加醋,相互传播,使得传闻愈发纷繁复杂。

在中共首个农村支部纪念馆中,矗立着一尊李大钊与弓仲韬握手的历史雕像。
人们愈是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便愈发渴望探知外面的世界;当视力受限时,对世间万象的好奇心更是难以遏制,失明的弓仲韬亦是如此。得知此事,他径直前往县委,在张根生、方纪、王林面前,愤然指责道:“你们侵占土改成果,这是人民和党所不容的。王林的毛大氅,必须查明真相,若是公家的,务必归还。张根生书记和县长,你们所涉的两件事,必须将钱财上交。这是党性问题,绝不能含糊其辞。”随后,方纪组织人员对王林的毛大氅一事展开调查,证实是其个人过往所购。张根生和县长也迅速将款项交至黄城土改工作队。此事过后,众人纷纷称赞弓仲韬是一位虽眼盲却心明如镜,党性原则尤为坚定的英雄。
弓仲韬是那类人。
1948年2月5日,王林的日记记载:“……在上午,我与梁斌一同造访台城。弓仲韬听闻我们的到来,即刻说道:‘我这里的空气不佳,你们赶紧离开。’即便我们解释,他也固执己见。这一情形充分证实了,那日我们在齐岩南处所见的那位女子,正是赵容之。原来,她昨日曾为弓仲韬传信至齐处。弓仲韬自地委回来,得知我前访,却未与他相见,由此心生不悦。”由此可见,当时王林与弓仲韬的关系颇为融洽。据王林所述,张根生、王林、孙犁、梁斌、方纪等人当时均与弓仲韬相识,且众人对他都颇为尊敬。然而,由于当时大家均忙于现实工作,创作焦点也主要集中在抗战题材,因此在其他方面并未留下过多文字。
1945年5月24日,安平县城宣告解放。得益于解放的早先优势,土改工作得以提前布局。同年9月,安平县便全面启动了土地改革工作。王林与方纪均积极参与了安平土地改革的领导工作,其中王林更是身兼黄城片区土改工作队队长一职。
在黄城担任土改工作队长的那段时光里,王林与弓仲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能力范围内给予了弓仲韬政治及生活上的关照,让弓仲韬感受到了温暖与关怀。那时,弓仲韬因多年来的艰难历程与挫折,已将个人故事深埋心底,不愿再向他人透露。彼时的弓仲韬生活困顿,视力丧失,性情亦变得颇为急躁,众人不自觉地与他拉开了距离。

弓仲韬晚年与女儿弓乃如。
随着全国抗战的爆发,1937年9月的一个清晨,弓仲韬怀抱革命理想,携母亲、妻子李俊阁、妹妹弓翟芳、女儿弓乃如及侄子弓惠霆,一家六口踏上前往延安的征程。抵达西安后,因种种变故,他们滞留了长达六年。岁月更迭,至1943年秋,弓仲韬孤身一人,又瞎又病,生活困苦不堪。他向友人吐露心声,渴望返回故乡。得知此事后,友人们商议一番,决定接力将弓仲韬从西安送回安平故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终于将弓仲韬安全送达安平。在抵达台城之前,弓仲韬恳请友人先送他至深县唐奉眼科医院,以期治愈眼疾。然而,医生检查后告知,其眼底及眼球组织已严重坏死,无法救治。无奈之下,人们只得将他送回台城村。村民们见到他时,不禁想起他离家时那年轻有为、健壮如牛的形象。如今,他已面黄肌瘦,形销骨立,面目全非。面对这样的他,村民们不知如何安慰,只能默默转身,暗自垂泪。六年前,他带着母亲、妻子、大妹、侄儿、女儿,一家六口从台城出发,心怀炽热的革命信念。途中,钱财被土匪洗劫一空,抵达西安后,举目无亲,生活陷入困境。首先,母亲、大妹和侄儿不得不离开他们前往重庆。离别那天,一家人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女儿为寻找前往延安的路线,四处奔波,日夜不停。后来,妻子因病无钱治疗而离世,连一口薄棺都难以购置,只得用一张旧席片包裹遗体,就地埋葬。他自己外出打工,因宣传革命思想,遭到工厂主的残酷迫害,双眼失明。这些年来,他在艰难的生存中饱受屈辱。六年间,他经历了无数艰辛与苦难,数次险些命丧黄泉。六年后,当他重返老宅,眼前一片漆黑,家人已离散。在大门口,他拒绝他人的搀扶,摸索着大门,最终倒在地上,一瘸一拐地爬进院子里。他激动地拍打着院中的土地,放声大哭,那悲怆的哭声传遍了附近的每家每户。
弓仲韬一直怀揣着治愈双眼的愿望,渴望能为党和人民贡献更多力量。于是,他恳请王林为他寻得一线生机。为此,王林不辞辛劳,特地走访了深县的唐奉眼科医院以及邢台的几家眼科医院,然而,由于病情已至晚期,治愈无望,各家医院均无奈地表示,无力回天。
“这哪里是出身豪门的公子哥儿,你这完全是革命队伍中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啊!”
在黄城负责土地改革工作期间,王林每当接到弓仲韬的汇报与难题,总是迅速亲自前往台城进行处置。他不止一次地向台城村长杨栓强调,对弓仲韬这位资深党员应给予适当的关照,毕竟他年事已高,视力与听力皆受限,我们绝不能让这样一位资深同志遭受不公与欺凌。针对弓仲韬反映的村治安员弓春生性格刚直,因而得罪了众多人,导致其无法加入贫民组的问题,王林亲自与弓春生进行了谈话,指导他改进工作方式,并适时安排他参加了区里举办的培训班。
王林在日记中由衷地赞叹:“弓仲韬的正义感尤为强烈。”弓仲韬在审视问题、陈述事实时,总是以党性为衡量准则,作为评判的标准。王林曾言,弓仲韬坚定不移的党性精神,值得我们深入学习与效仿。

在1947年9月30日的日记中,王林记录了弓仲韬提及的入党经历:“弓仲韬于民国十二年正月入党”,即1923年。当时弓仲韬在北京北沙滩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师,该校与红楼北大图书馆相邻,他与李大钊时有会面。弓仲韬向王林透露,他在正月十五日,即李大钊家中被介绍入党。李大钊在宣布入党后,向弓仲韬传授了一些注意事项,并嘱咐他迅速返回家乡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础组织。那天,他们共同享用的是李大钊购买的汤圆,一大锅的汤圆煮得丰盛。送别弓仲韬时,李大钊告知他:“我马上就要出发了。”这是王林对弓仲韬回忆的描述。经过核实,民国十二年正月十五,即1923年3月2日,这一日期与现有档案资料和回忆录基本吻合。王洁编写的《李大钊北京十年——事件篇》一书中第142页明确指出:“1923年3月,李大钊介绍弓仲韬入党。”那么,关于1923年3月2日这一具体日期李大钊介绍弓仲韬入党的事实是否与历史相符?
当时正值1923年2月,“二七惨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震动。紧随其后,北京政府下达了对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通缉令。在此期间,李大钊大部分时间不在首都北京,而是流亡至上海。
据所搜集的信息,早在3月2日之前,已有确切消息指出:1923年年初,李大钊便离开了京城,踏上了前往武汉的讲学之旅。2月4日的傍晚,即下午7点至9点之间,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的盛情邀请,李大钊在寒假期间的演讲会上,发表了题为“当前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与性质,以及我国妇女应采取的推进策略”的精彩演讲。
法界环龙路44号,由张春木代转。经过核实,这一地址实为《新青年》杂志社所在地,而张春木则是张太雷的化名。
“1923年3月30日,亨得利克斯·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于李大钊寓所主持了一场会议,旨在研讨党内若干工作事宜。张太雷等同志亦参与了此次会议。”
据此推断,李大钊于3月2日返回北京以处理相关事务,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①依据李运昌同志的回忆录,李锡九、弓仲韬二同志系由李大钊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我坚信李运昌深得李大钊的信赖。李大钊曾有意让李运昌返回故乡,在农村地区发展党组织,因此,他与李运昌探讨李锡九和弓仲韬的入党事宜及在农村建立党组织的话题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在法律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的、共计42万字的《李运昌回忆录》中,并未提及这一事件。可能的原因是,这与李锡九的党员身份未对外公开有关。李锡九于1922年2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任务要求他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不透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解放后的多年里,李锡九都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现在各类场合和会议上。

◆弓仲韬
“李永声(1872—1952),又名李锡九。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参与创建并领导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由此可以推断,李锡九的党员身份长期未被公开。李锡九与弓仲韬同是安平人士,均由李大钊引荐入党。
本文的起因源自王林同志所撰写的数篇日记,故此,在此我将对王林同志的生平事迹进行简略概述。
“这是对冀中人民的一首庄严而丰富的颂歌”,“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画卷”,“描绘一个伟大时代的风土人情,正是本书的生命之源。”
王林先生生前担任天津市总工会文教部长、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及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多重职务。其笔下作品丰富,创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腹地》、《站起来的人民》、《一二·九进行曲》和《叱咤风云》等,中篇小说如《夜明珠》、《五台山下》和《女村长》,以及短篇小说《十八匹战马》,后者被誉为二战期间的经典之作。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王林文集》。吕正操司令员曾深情地称赞王林为“冀中的活地图,冀中人民的儿子”。
王林,一位细腻用心的人,与他与弓仲韬的交往中,留下了几篇珍贵的日记。这些日记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认识弓仲韬,他是一位党性原则坚如磐石的人。在学习和铭记弓仲韬的精神的同时,我们亦应向王林先生表示由衷的感激。
我要配资网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